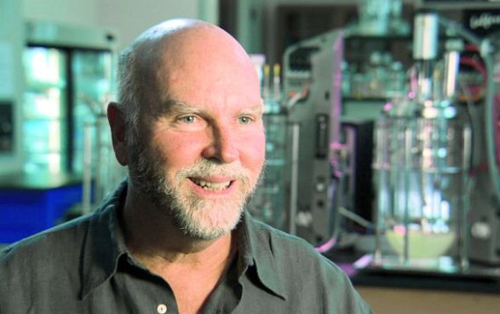
1998年,克雷格•文特尔创建的营利性公司塞雷拉基因组公司(Celera)向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于1985年率先提出,于1990年正式启动,旨在把人体内约4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谱图——译者注)发出挑战,与政府打了个平手,在当时引起轰动,而后却被公司解雇。如今,这位生物学家运营着一家非营利组织文特尔研究所和两家生物科技公司。文特尔的一生充满传奇,手下管理着大量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经历过职业低谷期,热衷航海、赛车等冒险活动,将之视为保持创造力的源泉。
HBR: 你的目标一贯大胆,但是你总能实现它。为什么?
文特尔:觉得目标大胆的是别人。我认为它们完全可以实现。人类基因组计划本来预计历时15年,预算达50亿美元。而一个小团队能用不到15年的时间,仅花费前者预算的一小部分就完成了该项目,这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但对我来说这个目标合情合理,因为我有一支非常出色的团队。我的一位老师曾戏言,这种做法就像是我从很高的跳台跃入一个干涸的泳池,在摔死前等着我的团队把水蓄上。
HBR:你甄选科学家和管理层的方法是什么?
文特尔:我在这两者之间看重的东西类似,因为我们管理层中大多是科学家。我们需要富有创造力、灵活性并能自我激励的人。我们选中的人通常喜欢难度很大的挑战,并知道他们所作的贡献可以改变世界。
HBR:你是哪种老板?
文特尔:无论他人怎么看,我不是一个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人,我善于放权。我尽量雇用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并给他们充分自由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我会制定目标和日程,但是如果涉及执行,要么由我们的团队共同决定,要么由项目负责人决定。我天生缺乏耐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已经有所进步——因为我逐渐发现事情不会按照我的节奏来,通常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当你和优秀的人共事时,他们通常很有耐心,因为大家知道事情已经按照最好的节奏进行,而且整个过程中不断伴随着令人兴奋的发现。
HBR:你和一些科学家合作长达数年,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文特尔:我认为长远来看,人们能够在我创造的环境中不断进步,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设终身职位。我们不像政府机构或高校,不会用这种奖励让一些人过早放弃奋斗。我们都知道,超越昨天的自己才是正道。真正优秀的人不会为获得安全感而奋斗,他们奋斗的动力是在学术上取得突破。
HBR:但你也与之前的研究伙伴或生意伙伴分道扬镳过,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与塞雷拉基因组公司的是是非非。这些经验教会了你什么?
文特尔:我没有主动离开塞雷拉,而是被解雇的。在我攻克了基因组排序,并筹集了10亿美元现金后,我显然对公司已没什么用了,当然部分也是因为我曾表示想回研究所,因此我被逼与塞雷拉“离婚”。不过,你会从这种变动中学到很多。这可能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之一,因为即使技术尚未成熟,我也很可能会在那里多呆好多年。塞雷拉基因组公司是革命的开始,但是15年时间还不足以令其改变医学面貌。
HBR:你也曾遭遇批评,面临职业生涯的低谷。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文特尔:你必须相信自己做的事,相信这一切都是过程。在越南服役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能够前往战场并得以生还是我的幸运。我很早就明白,人生最糟的事莫过于失去生命,冒险和遭遇挫折是让人前进的一部分。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懂的多是因为犯的错误多。眼光放长远也很重要。在我的新书《光速生活》中,我讨论了我们在首个合成细胞问世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政府通常不愿赞助这类研究,因为解决其中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我也曾怀疑自己无法说服执行委员会,让他们相信这些问题终将解决。但我一直坚信它们会被解决,惟有成功能证明一切。
HBR:人们谴责你将科学“商业化”。
文特尔:二战前,科学研究大都受到私企和慈善机构资助。之后我们迎来了美国政府大量资助科研的黄金期。但是现在从比例上来说,政府基金对科学项目的资助可以用惨淡来形容,政策也在限制创造力,所以商业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途径之一。商业是目标还是结果并无区别,因为科学要想影响社会,就必须能带来经济收益,比如说,药物必须有效和具有可及性。当政府表现令人失望时,私人投资是保证科学不断突破的一种方法。
HBR:你的爱好都充满风险:航海、骑摩托车、赛车。为什么?
文特尔:航海、骑摩托车或者开赛车可以被视为冒险行为。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就不是。我认为这些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活动,无论是否冒险,都可以让我清空大脑,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在效率低下时得以喘息。对我来说,这是保持创造性的关键。

